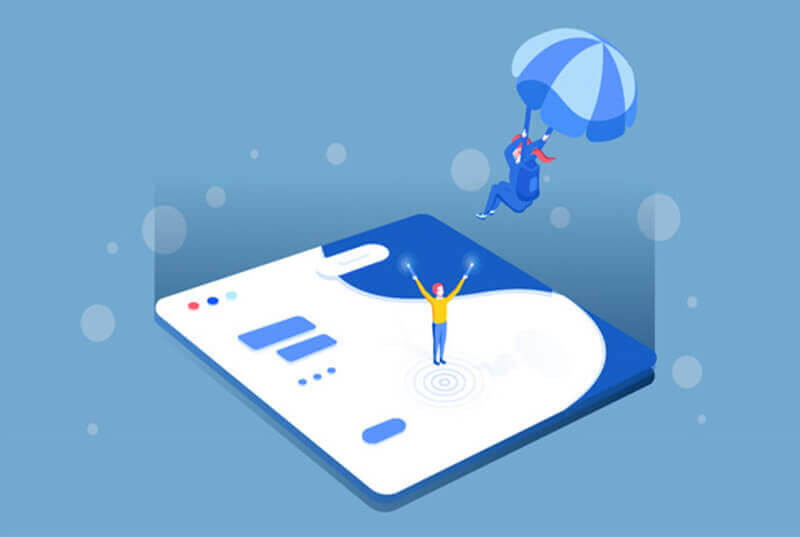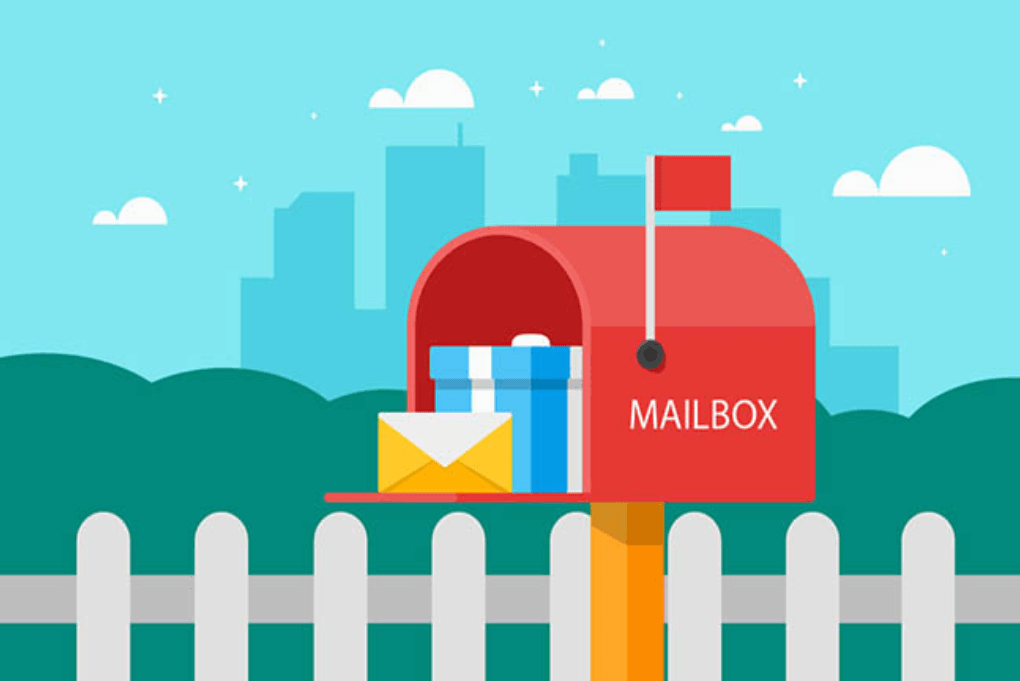搜索到
2
篇与
的结果
-
 能翻译中文圣经的美国人,是怎么学习汉语的? 最近在读丁韪良所著的《花甲记忆》,里面有一章专门写到他是如何学习汉语的,给我启发很大。丁韪良是美国长老会传教士、外交官、教育家,晚清时期在中国活动的重要人物。和近代很多来华的传教士一样,他是一个中国通。他1850年左右先来到宁波,开始学宁波话,六个月之后就可以用宁波话讲道,后来他又学会了北方的官话,得以成为美国公使跟清朝官员谈判的翻译,再后来,他成为京师同文馆和京师大学堂(北大前身)的总教习,为当时的中国培养了首批外语和科技人才,推动现代学科体系的建立。我喜欢阅读来华传教士的传记,会特别关注他们是怎么学习汉语的,因为我对语言学习非常感兴趣。应该说,丁韪良的语言学习效果非常卓著,无数跟他一样来华的西方人,也都能在短短几个月内掌握当地的语言,从而实现交流。我说的当地语言往往指的是方言,而非我们现在的普通话。我们现在所读的和合本圣经当年就是一群美国人翻译的,他们究竟是怎么学习中文的?不得不说,他们是掌握了外语学习秘诀的人。那是一百多年前啊,没有像样的教材,更没有任何电子媒介,很多人来华之前,对汉语一窍不通,却能在短短数月内实现交流,时间长了就成为渊博的汉学家,能将圣经翻译成如此优美的中文,有的后来还被西方知名的大学聘请为汉语教授。一百多年后的今天,我们的学生苦学了十几年英语,却不能实现英语交流,可见我们的学习方法错得多么离谱,这也正是我花了很长时间去研究的一个主题。为什么在学习资源如此丰富的今天,我们的学生学不好英语呢?因为我们并没有掌握语言学习的秘诀啊。首先,任何语言的本质都是声音的交流,学习语言就是要先学声音。丁韪良刚来宁波时,请来的汉语老师是不懂英语的本地人,老师指着一件物品发出声音,丁韪良就跟着念,这就是学习声音。实现交流的前提是建立声音和意义的直接联系,听到声音就能想起相应的意义,这才是学习语言的正确进路。反观我们是怎么学习英语的?读写先行,建立的不是声音和意义的直接联系,而是声音和拼写之间的直接联系,背单词学语法,大脑里储存了一大堆英文符号,却没有储存有意义的英语声音,当然听不懂也说不出。其实,我们学习英语一直都注重读写和翻译,不注重听和说,这种方法称为“语法翻译法”,用这种方法学习任何外语,结果都是聋哑外语,不能实现声音交流。英语是拼音文字,重音不重形,英语为母语的人很多人都有阅读障碍,只能通过听来学习,但并不妨碍他们成才,就连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的拼写都是经常有错误的,但并不妨碍读者理解他的意思,也不妨碍他成为总统。学习英语,掌握声音是最重要的,掌握了听说,拼写就简单多了,特别是对于习惯认字的中国人来说,听力能力能向阅读能力转化,反之则不能。中文则是象形文字,重形不重音,我们可以互相听不懂对方的方言,但没有关系,能写就行,所以识字是一个千古执念,书法是每个读书人的必修课。我们读书时,英语老师要求我们要把英语单词写得工整好看,其实对于学习英语一点作用也没有。正是因为拥有英文大脑的丁韪良们善长从声音学习语言,所以他们无论在中国哪个地方学习哪种方言,都能很快掌握,前期不会浪费时间在读写上面,等到听说流利了之后,再来学习文字,日益精进,终成中国通。同样,我们学习英语,前期应该彻底放弃学习读写,只练听说。这正是我教我儿子学习英语的方法。在他六岁前,他不会让他学习认字,只让他听和说。他三岁多我开始教他英语,现在他的英语听说能力,已经比我大学毕业时的程度要好,而他还不到五岁,我说的一点都不夸张,他已经掌握英语的声音,能够如母语者一样用英语进行思考和交流了。要做到这一点,我总结需要做到以下步骤:一、大量地输入孩子可理解的听力内容。二、能理解的听力内容要在不同的场景中被反复听到。三、在前两项的基础上,要适当地增加语言的难度,让孩子不断进步。除了学习方法之外,学习动机和目的也是帮助丁韪良们快速学好汉语的关键。他们的目的很明确,就是要用当地的语言宣教,所以必须要学会外语。迫切的动机和明确的目的对学习外语大有益处。反观我们为什么要学习英语呢?我相信很多学校的英语老师都是不清楚的,非但不清楚,他们也不知道英语有什么用,他们没有读过英语原版书,没有用英语跟外国人交流过,也没能不借助字幕看懂一部英语电影。过去我在培训行业工作,接触过太多不合格的英语老师了,很多过了专八的英专学生,英语交流能力也很差。这也不奇怪,因为我们英语教育的目的,就是为了通过考试。用这个目的来指导学习,学十年的效果也没有丁韪良们学习十个月的效果强。最后,信心也是很重要的。具有虔诚信仰的丁韪良们是带着使命来到中国的,他们是怀着信心来的,很多人来了,就没有想着再回去。他们踏上中国土地的那一刻,就决定将生命奉献在这里,今天,在中国的土地上,可以找到很多他们的墓葬。他们学习汉语当然也是信心满满的,他们相信自己一定能学成,因为差遣他们来的那一位,一定会帮助他们学好语言,事实上也正是如此。阅读丁韪良的《花甲记忆》,还有一个感想,就是他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认识非常深刻,值得我们细细阅读。事实上,很多跟丁韪良一样带着使命来中国的西方人,都能深刻地理解中国,因为他们在用生命爱中国。他们的作品,我们应该找来读读,有助于我们理解自己的国家,也有助于我们睁眼看世界。我们真的很需要睁眼看世界。作者:马丁弟兄
能翻译中文圣经的美国人,是怎么学习汉语的? 最近在读丁韪良所著的《花甲记忆》,里面有一章专门写到他是如何学习汉语的,给我启发很大。丁韪良是美国长老会传教士、外交官、教育家,晚清时期在中国活动的重要人物。和近代很多来华的传教士一样,他是一个中国通。他1850年左右先来到宁波,开始学宁波话,六个月之后就可以用宁波话讲道,后来他又学会了北方的官话,得以成为美国公使跟清朝官员谈判的翻译,再后来,他成为京师同文馆和京师大学堂(北大前身)的总教习,为当时的中国培养了首批外语和科技人才,推动现代学科体系的建立。我喜欢阅读来华传教士的传记,会特别关注他们是怎么学习汉语的,因为我对语言学习非常感兴趣。应该说,丁韪良的语言学习效果非常卓著,无数跟他一样来华的西方人,也都能在短短几个月内掌握当地的语言,从而实现交流。我说的当地语言往往指的是方言,而非我们现在的普通话。我们现在所读的和合本圣经当年就是一群美国人翻译的,他们究竟是怎么学习中文的?不得不说,他们是掌握了外语学习秘诀的人。那是一百多年前啊,没有像样的教材,更没有任何电子媒介,很多人来华之前,对汉语一窍不通,却能在短短数月内实现交流,时间长了就成为渊博的汉学家,能将圣经翻译成如此优美的中文,有的后来还被西方知名的大学聘请为汉语教授。一百多年后的今天,我们的学生苦学了十几年英语,却不能实现英语交流,可见我们的学习方法错得多么离谱,这也正是我花了很长时间去研究的一个主题。为什么在学习资源如此丰富的今天,我们的学生学不好英语呢?因为我们并没有掌握语言学习的秘诀啊。首先,任何语言的本质都是声音的交流,学习语言就是要先学声音。丁韪良刚来宁波时,请来的汉语老师是不懂英语的本地人,老师指着一件物品发出声音,丁韪良就跟着念,这就是学习声音。实现交流的前提是建立声音和意义的直接联系,听到声音就能想起相应的意义,这才是学习语言的正确进路。反观我们是怎么学习英语的?读写先行,建立的不是声音和意义的直接联系,而是声音和拼写之间的直接联系,背单词学语法,大脑里储存了一大堆英文符号,却没有储存有意义的英语声音,当然听不懂也说不出。其实,我们学习英语一直都注重读写和翻译,不注重听和说,这种方法称为“语法翻译法”,用这种方法学习任何外语,结果都是聋哑外语,不能实现声音交流。英语是拼音文字,重音不重形,英语为母语的人很多人都有阅读障碍,只能通过听来学习,但并不妨碍他们成才,就连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的拼写都是经常有错误的,但并不妨碍读者理解他的意思,也不妨碍他成为总统。学习英语,掌握声音是最重要的,掌握了听说,拼写就简单多了,特别是对于习惯认字的中国人来说,听力能力能向阅读能力转化,反之则不能。中文则是象形文字,重形不重音,我们可以互相听不懂对方的方言,但没有关系,能写就行,所以识字是一个千古执念,书法是每个读书人的必修课。我们读书时,英语老师要求我们要把英语单词写得工整好看,其实对于学习英语一点作用也没有。正是因为拥有英文大脑的丁韪良们善长从声音学习语言,所以他们无论在中国哪个地方学习哪种方言,都能很快掌握,前期不会浪费时间在读写上面,等到听说流利了之后,再来学习文字,日益精进,终成中国通。同样,我们学习英语,前期应该彻底放弃学习读写,只练听说。这正是我教我儿子学习英语的方法。在他六岁前,他不会让他学习认字,只让他听和说。他三岁多我开始教他英语,现在他的英语听说能力,已经比我大学毕业时的程度要好,而他还不到五岁,我说的一点都不夸张,他已经掌握英语的声音,能够如母语者一样用英语进行思考和交流了。要做到这一点,我总结需要做到以下步骤:一、大量地输入孩子可理解的听力内容。二、能理解的听力内容要在不同的场景中被反复听到。三、在前两项的基础上,要适当地增加语言的难度,让孩子不断进步。除了学习方法之外,学习动机和目的也是帮助丁韪良们快速学好汉语的关键。他们的目的很明确,就是要用当地的语言宣教,所以必须要学会外语。迫切的动机和明确的目的对学习外语大有益处。反观我们为什么要学习英语呢?我相信很多学校的英语老师都是不清楚的,非但不清楚,他们也不知道英语有什么用,他们没有读过英语原版书,没有用英语跟外国人交流过,也没能不借助字幕看懂一部英语电影。过去我在培训行业工作,接触过太多不合格的英语老师了,很多过了专八的英专学生,英语交流能力也很差。这也不奇怪,因为我们英语教育的目的,就是为了通过考试。用这个目的来指导学习,学十年的效果也没有丁韪良们学习十个月的效果强。最后,信心也是很重要的。具有虔诚信仰的丁韪良们是带着使命来到中国的,他们是怀着信心来的,很多人来了,就没有想着再回去。他们踏上中国土地的那一刻,就决定将生命奉献在这里,今天,在中国的土地上,可以找到很多他们的墓葬。他们学习汉语当然也是信心满满的,他们相信自己一定能学成,因为差遣他们来的那一位,一定会帮助他们学好语言,事实上也正是如此。阅读丁韪良的《花甲记忆》,还有一个感想,就是他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认识非常深刻,值得我们细细阅读。事实上,很多跟丁韪良一样带着使命来中国的西方人,都能深刻地理解中国,因为他们在用生命爱中国。他们的作品,我们应该找来读读,有助于我们理解自己的国家,也有助于我们睁眼看世界。我们真的很需要睁眼看世界。作者:马丁弟兄 -
 苏联短暂的一生,竟然树立了386个官方学习榜样 在冬宫博物馆的苏联展厅,有许多褪色的劳动奖状,以及生锈的镰刀锤子徽章。从不屈的斗士保尔柯察金,到煤矿铁人斯达汉诺夫,从举报父亲的小英雄巴甫列克,到生了12个孩子的英雄母亲德米特里耶娃。苏联短暂的一生,竟然树立了386个官方榜样。保尔·柯察金,承载着我们几代人的集体记忆,曾经很长时间内都被当做苏联人的写实形象。但解密的资料却显示,奥斯特洛夫斯基创作的保尔形象,被苏联内务委强行做了7次重大修改。比如苏联红军之父托洛茨基的内容全部被删除,主人公对苏联红军的批评同样被全部清除,反而代之以不断强化的忠诚。还比如主人公原本赞成新经济政策,结果修改为反对新经济政策,拥抱计划经济。因此所谓的学习榜样,不过是被精心雕琢的盆景,是被权力意志操控的提线木偶。苏联庞大的官方榜样群像,折射的不是人性的光辉,而是权力对人性的规训,是权力机器对精神世界的操控。原版的保尔·柯察金,有理想、有爱恨,敢于针砭时弊,勇于表达个性,是一个对美好生活充满向往的现实青年,结果却被扭曲成了崇拜意识形态的圣徒,泯灭了个性意识,成为了一颗没有思想的螺丝钉。苏联的榜样文学,便是将复杂的人性简化为意识形态的符号。正如被誉为俄罗斯良心的索尔仁尼琴所说:他们需要的不是活生生的英雄,而是不会说话的纪念碑。苏俄的造神工程,始于1917年10月。苏布建政的当月,列氏便被捧为俄罗斯民族的救世主。苏俄的制度化造神开始于1920年,服装、领巾、语录、头像等等一应俱全,而且苏俄的意识形态,也拥有了第二个名称。1934年9月1日,苏联作协成立。从此之后,苏联的文学艺术便沦为了意识形态的传声筒。比如著名的《青年近卫军》,便按照苏联作协的指示,删除了主人公对集体化运动中大饥荒的不满。与苏联造神工程一同开始的,还有苏联的榜样工程。制度化的榜样工程开始于1927年,苏联的第一个官方榜样,便是煤矿铁人——斯达汉诺夫。顿巴斯的矿工斯达汉诺夫,在《真理报》的妙笔生花之下,竟然创下了一个人一天采煤20.4万斤的“壮举”,一个人相当于100名正常的工人。1935年,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了斯达汉诺夫。《真理报》的摄影师,特意拍摄了斯大林轻拍斯达汉诺夫肩膀的亲密画面。这个精心设计的场景,很快便通过《真理报》传遍了苏联,斯达汉诺夫成了苏联人的劳动榜样。可是,斯达汉诺夫的工作效率被宣传为常人的14倍,集体农庄里的农妇们为了完成超额的生产指标,只能饿着肚子把粮食上交。虽然人人都知道是在造假,但斯达汉诺夫的事迹依旧被包装为无产阶级觉悟的胜利。1935年,苏联开始在全国展播集体农庄的纪录片:金黄的麦浪中,女庄员们红润的脸庞洋溢着幸福的微笑。可是镜头外的现实却是,这些演员在拍摄结束后,需要立即归还借来的布拉吉连衣裙,赤脚走回漏风的木屋。这种榜样的宣传与现实的割裂,在1953年达到了顶点:当英雄母亲德米特里耶娃养育12个子女时,她只能用配给的肥皂票换黑面包,用以喂养营养不良的孩子们。1954年,赫鲁晓夫在苏布大会上公开指出:苏联集体农庄的劳动生产效率,只有美国家庭农场的17%。但同年上映的电影《库班哥萨克》,却把集体农庄描绘为流淌着牛奶与蜂蜜的世外桃源。正如著名的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,在《极端的年代》一书中的尖锐批评:苏联的乌托邦叙事,如同普洛克路斯忒斯之床,将现实裁剪得支离破碎。当先进工作者瓦西里每天工作16小时,却只能在日记里忏悔自己偷喝了儿子治病的牛奶。当顿巴斯的劳动模范尼古拉耶娃获得勋章的同时,却在举报车间主任破坏生产。这种认知体系的崩溃,在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披露后达到了高潮,原来斯大林时期的英雄榜样们,竟然都是虚假的宣传。1979年,苏联入侵阿富汗。《真理报》将阵亡的士兵包装为国际主义战士,而前线寄回的信件却在控诉战争的荒谬。1986年,苏联为切尔诺贝利事故中的相关人员授予了切尔诺贝利勋章,可是苏联的大学生们却成立了真实俱乐部,揭露了切尔诺贝利事故的真相。上世纪80年代,苏联虽然用黄金重塑了保尔的雕像,但这种价值的割裂,伴随着整个苏联大厦的裂痕,反而加速了民众的觉醒。尤日马什工厂的先进工作者彼得罗夫,便在日记中写道:当我第八次站在红旗勋章的领奖台上时,我突然意识到自己不过是一个提线木偶。正如柏林墙倒塌后东德青年的涂鸦:我们不需要水泥铸就的圣人,我们只要会犯错的活人。这些认知的裂缝,最终汇聚成了解体的洪流。在俄罗斯的旧货市场上,经常能看到苏维埃的勋章与东正教的圣像,它们经常被摆放在同一个摊位出售。这个荒诞的场景,正是苏联榜样工程的历史隐喻:当意识形态的圣徒像被赶下神坛,他们既不能回归人间成为真实的人,也无法升入天堂成为真正的神,只能作为历史的标本,在现实的橱窗里继续展览。那些被精心设计的学习榜样,既是权力艺术的巅峰之作,也是乌托邦工程最苦涩的墓志铭。当崇高的理想异化为意识形态的工具,那些被精心塑造的学习榜样,必将沦为历史废墟中的荒诞符号。正如平庸之恶的提出者阿伦特所说:任何试图用标准化人格塑造社会的努力,终将在人性的复杂面前碰得粉碎。作者:捉刀漫谈max
苏联短暂的一生,竟然树立了386个官方学习榜样 在冬宫博物馆的苏联展厅,有许多褪色的劳动奖状,以及生锈的镰刀锤子徽章。从不屈的斗士保尔柯察金,到煤矿铁人斯达汉诺夫,从举报父亲的小英雄巴甫列克,到生了12个孩子的英雄母亲德米特里耶娃。苏联短暂的一生,竟然树立了386个官方榜样。保尔·柯察金,承载着我们几代人的集体记忆,曾经很长时间内都被当做苏联人的写实形象。但解密的资料却显示,奥斯特洛夫斯基创作的保尔形象,被苏联内务委强行做了7次重大修改。比如苏联红军之父托洛茨基的内容全部被删除,主人公对苏联红军的批评同样被全部清除,反而代之以不断强化的忠诚。还比如主人公原本赞成新经济政策,结果修改为反对新经济政策,拥抱计划经济。因此所谓的学习榜样,不过是被精心雕琢的盆景,是被权力意志操控的提线木偶。苏联庞大的官方榜样群像,折射的不是人性的光辉,而是权力对人性的规训,是权力机器对精神世界的操控。原版的保尔·柯察金,有理想、有爱恨,敢于针砭时弊,勇于表达个性,是一个对美好生活充满向往的现实青年,结果却被扭曲成了崇拜意识形态的圣徒,泯灭了个性意识,成为了一颗没有思想的螺丝钉。苏联的榜样文学,便是将复杂的人性简化为意识形态的符号。正如被誉为俄罗斯良心的索尔仁尼琴所说:他们需要的不是活生生的英雄,而是不会说话的纪念碑。苏俄的造神工程,始于1917年10月。苏布建政的当月,列氏便被捧为俄罗斯民族的救世主。苏俄的制度化造神开始于1920年,服装、领巾、语录、头像等等一应俱全,而且苏俄的意识形态,也拥有了第二个名称。1934年9月1日,苏联作协成立。从此之后,苏联的文学艺术便沦为了意识形态的传声筒。比如著名的《青年近卫军》,便按照苏联作协的指示,删除了主人公对集体化运动中大饥荒的不满。与苏联造神工程一同开始的,还有苏联的榜样工程。制度化的榜样工程开始于1927年,苏联的第一个官方榜样,便是煤矿铁人——斯达汉诺夫。顿巴斯的矿工斯达汉诺夫,在《真理报》的妙笔生花之下,竟然创下了一个人一天采煤20.4万斤的“壮举”,一个人相当于100名正常的工人。1935年,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了斯达汉诺夫。《真理报》的摄影师,特意拍摄了斯大林轻拍斯达汉诺夫肩膀的亲密画面。这个精心设计的场景,很快便通过《真理报》传遍了苏联,斯达汉诺夫成了苏联人的劳动榜样。可是,斯达汉诺夫的工作效率被宣传为常人的14倍,集体农庄里的农妇们为了完成超额的生产指标,只能饿着肚子把粮食上交。虽然人人都知道是在造假,但斯达汉诺夫的事迹依旧被包装为无产阶级觉悟的胜利。1935年,苏联开始在全国展播集体农庄的纪录片:金黄的麦浪中,女庄员们红润的脸庞洋溢着幸福的微笑。可是镜头外的现实却是,这些演员在拍摄结束后,需要立即归还借来的布拉吉连衣裙,赤脚走回漏风的木屋。这种榜样的宣传与现实的割裂,在1953年达到了顶点:当英雄母亲德米特里耶娃养育12个子女时,她只能用配给的肥皂票换黑面包,用以喂养营养不良的孩子们。1954年,赫鲁晓夫在苏布大会上公开指出:苏联集体农庄的劳动生产效率,只有美国家庭农场的17%。但同年上映的电影《库班哥萨克》,却把集体农庄描绘为流淌着牛奶与蜂蜜的世外桃源。正如著名的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,在《极端的年代》一书中的尖锐批评:苏联的乌托邦叙事,如同普洛克路斯忒斯之床,将现实裁剪得支离破碎。当先进工作者瓦西里每天工作16小时,却只能在日记里忏悔自己偷喝了儿子治病的牛奶。当顿巴斯的劳动模范尼古拉耶娃获得勋章的同时,却在举报车间主任破坏生产。这种认知体系的崩溃,在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披露后达到了高潮,原来斯大林时期的英雄榜样们,竟然都是虚假的宣传。1979年,苏联入侵阿富汗。《真理报》将阵亡的士兵包装为国际主义战士,而前线寄回的信件却在控诉战争的荒谬。1986年,苏联为切尔诺贝利事故中的相关人员授予了切尔诺贝利勋章,可是苏联的大学生们却成立了真实俱乐部,揭露了切尔诺贝利事故的真相。上世纪80年代,苏联虽然用黄金重塑了保尔的雕像,但这种价值的割裂,伴随着整个苏联大厦的裂痕,反而加速了民众的觉醒。尤日马什工厂的先进工作者彼得罗夫,便在日记中写道:当我第八次站在红旗勋章的领奖台上时,我突然意识到自己不过是一个提线木偶。正如柏林墙倒塌后东德青年的涂鸦:我们不需要水泥铸就的圣人,我们只要会犯错的活人。这些认知的裂缝,最终汇聚成了解体的洪流。在俄罗斯的旧货市场上,经常能看到苏维埃的勋章与东正教的圣像,它们经常被摆放在同一个摊位出售。这个荒诞的场景,正是苏联榜样工程的历史隐喻:当意识形态的圣徒像被赶下神坛,他们既不能回归人间成为真实的人,也无法升入天堂成为真正的神,只能作为历史的标本,在现实的橱窗里继续展览。那些被精心设计的学习榜样,既是权力艺术的巅峰之作,也是乌托邦工程最苦涩的墓志铭。当崇高的理想异化为意识形态的工具,那些被精心塑造的学习榜样,必将沦为历史废墟中的荒诞符号。正如平庸之恶的提出者阿伦特所说:任何试图用标准化人格塑造社会的努力,终将在人性的复杂面前碰得粉碎。作者:捉刀漫谈max