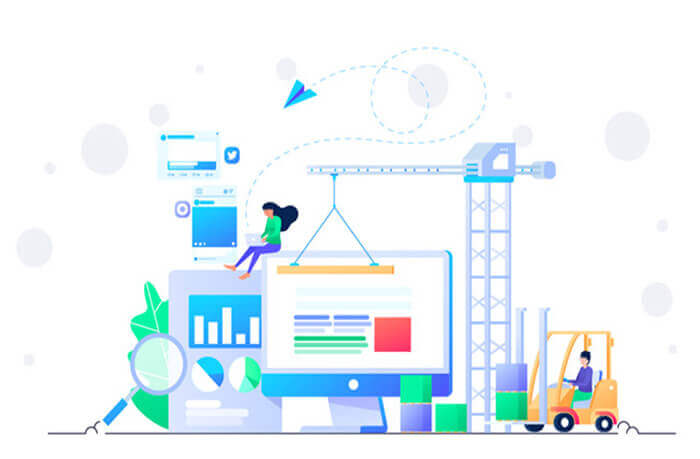搜索到
2
篇与
的结果
-
 苏联短暂的一生,竟然树立了386个官方学习榜样 在冬宫博物馆的苏联展厅,有许多褪色的劳动奖状,以及生锈的镰刀锤子徽章。从不屈的斗士保尔柯察金,到煤矿铁人斯达汉诺夫,从举报父亲的小英雄巴甫列克,到生了12个孩子的英雄母亲德米特里耶娃。苏联短暂的一生,竟然树立了386个官方榜样。保尔·柯察金,承载着我们几代人的集体记忆,曾经很长时间内都被当做苏联人的写实形象。但解密的资料却显示,奥斯特洛夫斯基创作的保尔形象,被苏联内务委强行做了7次重大修改。比如苏联红军之父托洛茨基的内容全部被删除,主人公对苏联红军的批评同样被全部清除,反而代之以不断强化的忠诚。还比如主人公原本赞成新经济政策,结果修改为反对新经济政策,拥抱计划经济。因此所谓的学习榜样,不过是被精心雕琢的盆景,是被权力意志操控的提线木偶。苏联庞大的官方榜样群像,折射的不是人性的光辉,而是权力对人性的规训,是权力机器对精神世界的操控。原版的保尔·柯察金,有理想、有爱恨,敢于针砭时弊,勇于表达个性,是一个对美好生活充满向往的现实青年,结果却被扭曲成了崇拜意识形态的圣徒,泯灭了个性意识,成为了一颗没有思想的螺丝钉。苏联的榜样文学,便是将复杂的人性简化为意识形态的符号。正如被誉为俄罗斯良心的索尔仁尼琴所说:他们需要的不是活生生的英雄,而是不会说话的纪念碑。苏俄的造神工程,始于1917年10月。苏布建政的当月,列氏便被捧为俄罗斯民族的救世主。苏俄的制度化造神开始于1920年,服装、领巾、语录、头像等等一应俱全,而且苏俄的意识形态,也拥有了第二个名称。1934年9月1日,苏联作协成立。从此之后,苏联的文学艺术便沦为了意识形态的传声筒。比如著名的《青年近卫军》,便按照苏联作协的指示,删除了主人公对集体化运动中大饥荒的不满。与苏联造神工程一同开始的,还有苏联的榜样工程。制度化的榜样工程开始于1927年,苏联的第一个官方榜样,便是煤矿铁人——斯达汉诺夫。顿巴斯的矿工斯达汉诺夫,在《真理报》的妙笔生花之下,竟然创下了一个人一天采煤20.4万斤的“壮举”,一个人相当于100名正常的工人。1935年,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了斯达汉诺夫。《真理报》的摄影师,特意拍摄了斯大林轻拍斯达汉诺夫肩膀的亲密画面。这个精心设计的场景,很快便通过《真理报》传遍了苏联,斯达汉诺夫成了苏联人的劳动榜样。可是,斯达汉诺夫的工作效率被宣传为常人的14倍,集体农庄里的农妇们为了完成超额的生产指标,只能饿着肚子把粮食上交。虽然人人都知道是在造假,但斯达汉诺夫的事迹依旧被包装为无产阶级觉悟的胜利。1935年,苏联开始在全国展播集体农庄的纪录片:金黄的麦浪中,女庄员们红润的脸庞洋溢着幸福的微笑。可是镜头外的现实却是,这些演员在拍摄结束后,需要立即归还借来的布拉吉连衣裙,赤脚走回漏风的木屋。这种榜样的宣传与现实的割裂,在1953年达到了顶点:当英雄母亲德米特里耶娃养育12个子女时,她只能用配给的肥皂票换黑面包,用以喂养营养不良的孩子们。1954年,赫鲁晓夫在苏布大会上公开指出:苏联集体农庄的劳动生产效率,只有美国家庭农场的17%。但同年上映的电影《库班哥萨克》,却把集体农庄描绘为流淌着牛奶与蜂蜜的世外桃源。正如著名的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,在《极端的年代》一书中的尖锐批评:苏联的乌托邦叙事,如同普洛克路斯忒斯之床,将现实裁剪得支离破碎。当先进工作者瓦西里每天工作16小时,却只能在日记里忏悔自己偷喝了儿子治病的牛奶。当顿巴斯的劳动模范尼古拉耶娃获得勋章的同时,却在举报车间主任破坏生产。这种认知体系的崩溃,在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披露后达到了高潮,原来斯大林时期的英雄榜样们,竟然都是虚假的宣传。1979年,苏联入侵阿富汗。《真理报》将阵亡的士兵包装为国际主义战士,而前线寄回的信件却在控诉战争的荒谬。1986年,苏联为切尔诺贝利事故中的相关人员授予了切尔诺贝利勋章,可是苏联的大学生们却成立了真实俱乐部,揭露了切尔诺贝利事故的真相。上世纪80年代,苏联虽然用黄金重塑了保尔的雕像,但这种价值的割裂,伴随着整个苏联大厦的裂痕,反而加速了民众的觉醒。尤日马什工厂的先进工作者彼得罗夫,便在日记中写道:当我第八次站在红旗勋章的领奖台上时,我突然意识到自己不过是一个提线木偶。正如柏林墙倒塌后东德青年的涂鸦:我们不需要水泥铸就的圣人,我们只要会犯错的活人。这些认知的裂缝,最终汇聚成了解体的洪流。在俄罗斯的旧货市场上,经常能看到苏维埃的勋章与东正教的圣像,它们经常被摆放在同一个摊位出售。这个荒诞的场景,正是苏联榜样工程的历史隐喻:当意识形态的圣徒像被赶下神坛,他们既不能回归人间成为真实的人,也无法升入天堂成为真正的神,只能作为历史的标本,在现实的橱窗里继续展览。那些被精心设计的学习榜样,既是权力艺术的巅峰之作,也是乌托邦工程最苦涩的墓志铭。当崇高的理想异化为意识形态的工具,那些被精心塑造的学习榜样,必将沦为历史废墟中的荒诞符号。正如平庸之恶的提出者阿伦特所说:任何试图用标准化人格塑造社会的努力,终将在人性的复杂面前碰得粉碎。作者:捉刀漫谈max
苏联短暂的一生,竟然树立了386个官方学习榜样 在冬宫博物馆的苏联展厅,有许多褪色的劳动奖状,以及生锈的镰刀锤子徽章。从不屈的斗士保尔柯察金,到煤矿铁人斯达汉诺夫,从举报父亲的小英雄巴甫列克,到生了12个孩子的英雄母亲德米特里耶娃。苏联短暂的一生,竟然树立了386个官方榜样。保尔·柯察金,承载着我们几代人的集体记忆,曾经很长时间内都被当做苏联人的写实形象。但解密的资料却显示,奥斯特洛夫斯基创作的保尔形象,被苏联内务委强行做了7次重大修改。比如苏联红军之父托洛茨基的内容全部被删除,主人公对苏联红军的批评同样被全部清除,反而代之以不断强化的忠诚。还比如主人公原本赞成新经济政策,结果修改为反对新经济政策,拥抱计划经济。因此所谓的学习榜样,不过是被精心雕琢的盆景,是被权力意志操控的提线木偶。苏联庞大的官方榜样群像,折射的不是人性的光辉,而是权力对人性的规训,是权力机器对精神世界的操控。原版的保尔·柯察金,有理想、有爱恨,敢于针砭时弊,勇于表达个性,是一个对美好生活充满向往的现实青年,结果却被扭曲成了崇拜意识形态的圣徒,泯灭了个性意识,成为了一颗没有思想的螺丝钉。苏联的榜样文学,便是将复杂的人性简化为意识形态的符号。正如被誉为俄罗斯良心的索尔仁尼琴所说:他们需要的不是活生生的英雄,而是不会说话的纪念碑。苏俄的造神工程,始于1917年10月。苏布建政的当月,列氏便被捧为俄罗斯民族的救世主。苏俄的制度化造神开始于1920年,服装、领巾、语录、头像等等一应俱全,而且苏俄的意识形态,也拥有了第二个名称。1934年9月1日,苏联作协成立。从此之后,苏联的文学艺术便沦为了意识形态的传声筒。比如著名的《青年近卫军》,便按照苏联作协的指示,删除了主人公对集体化运动中大饥荒的不满。与苏联造神工程一同开始的,还有苏联的榜样工程。制度化的榜样工程开始于1927年,苏联的第一个官方榜样,便是煤矿铁人——斯达汉诺夫。顿巴斯的矿工斯达汉诺夫,在《真理报》的妙笔生花之下,竟然创下了一个人一天采煤20.4万斤的“壮举”,一个人相当于100名正常的工人。1935年,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了斯达汉诺夫。《真理报》的摄影师,特意拍摄了斯大林轻拍斯达汉诺夫肩膀的亲密画面。这个精心设计的场景,很快便通过《真理报》传遍了苏联,斯达汉诺夫成了苏联人的劳动榜样。可是,斯达汉诺夫的工作效率被宣传为常人的14倍,集体农庄里的农妇们为了完成超额的生产指标,只能饿着肚子把粮食上交。虽然人人都知道是在造假,但斯达汉诺夫的事迹依旧被包装为无产阶级觉悟的胜利。1935年,苏联开始在全国展播集体农庄的纪录片:金黄的麦浪中,女庄员们红润的脸庞洋溢着幸福的微笑。可是镜头外的现实却是,这些演员在拍摄结束后,需要立即归还借来的布拉吉连衣裙,赤脚走回漏风的木屋。这种榜样的宣传与现实的割裂,在1953年达到了顶点:当英雄母亲德米特里耶娃养育12个子女时,她只能用配给的肥皂票换黑面包,用以喂养营养不良的孩子们。1954年,赫鲁晓夫在苏布大会上公开指出:苏联集体农庄的劳动生产效率,只有美国家庭农场的17%。但同年上映的电影《库班哥萨克》,却把集体农庄描绘为流淌着牛奶与蜂蜜的世外桃源。正如著名的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,在《极端的年代》一书中的尖锐批评:苏联的乌托邦叙事,如同普洛克路斯忒斯之床,将现实裁剪得支离破碎。当先进工作者瓦西里每天工作16小时,却只能在日记里忏悔自己偷喝了儿子治病的牛奶。当顿巴斯的劳动模范尼古拉耶娃获得勋章的同时,却在举报车间主任破坏生产。这种认知体系的崩溃,在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披露后达到了高潮,原来斯大林时期的英雄榜样们,竟然都是虚假的宣传。1979年,苏联入侵阿富汗。《真理报》将阵亡的士兵包装为国际主义战士,而前线寄回的信件却在控诉战争的荒谬。1986年,苏联为切尔诺贝利事故中的相关人员授予了切尔诺贝利勋章,可是苏联的大学生们却成立了真实俱乐部,揭露了切尔诺贝利事故的真相。上世纪80年代,苏联虽然用黄金重塑了保尔的雕像,但这种价值的割裂,伴随着整个苏联大厦的裂痕,反而加速了民众的觉醒。尤日马什工厂的先进工作者彼得罗夫,便在日记中写道:当我第八次站在红旗勋章的领奖台上时,我突然意识到自己不过是一个提线木偶。正如柏林墙倒塌后东德青年的涂鸦:我们不需要水泥铸就的圣人,我们只要会犯错的活人。这些认知的裂缝,最终汇聚成了解体的洪流。在俄罗斯的旧货市场上,经常能看到苏维埃的勋章与东正教的圣像,它们经常被摆放在同一个摊位出售。这个荒诞的场景,正是苏联榜样工程的历史隐喻:当意识形态的圣徒像被赶下神坛,他们既不能回归人间成为真实的人,也无法升入天堂成为真正的神,只能作为历史的标本,在现实的橱窗里继续展览。那些被精心设计的学习榜样,既是权力艺术的巅峰之作,也是乌托邦工程最苦涩的墓志铭。当崇高的理想异化为意识形态的工具,那些被精心塑造的学习榜样,必将沦为历史废墟中的荒诞符号。正如平庸之恶的提出者阿伦特所说:任何试图用标准化人格塑造社会的努力,终将在人性的复杂面前碰得粉碎。作者:捉刀漫谈max -
 人类文明的瑰宝:苏联笑话 最近有粉丝私信抱怨说:“关注你太亏了,你都不能做到日更。”还有粉丝上周日留言:“终于又写长文了。”言外之意我之前那种动辄数千字的长文写的不多了。没错,这点我承认,但我也有无奈和苦衷。就拿昨天来说,我辛辛苦苦码了6000多字,结果一发——直接被拦,怎么改都不行;周一那篇写三百多年前“自挂煤山东南枝”人物的文章,洋洋洒洒5000多字,也发不出去。搞得我写东西都像在拆盲盒,写完了还得祈祷能过参茶,这种把自己辛苦的结晶交给别人决定命运的玩法,一度让我想放弃,后来还是在那位指导我这张又红又专首图的前辈点拨下,让我把打赏开了,用他原话说:“我就没见过谁和钱过不去的。“所以,朋友们,别怪我不写(其实周末我一般会喝大酒,确实懒得写),实在是我有时候就算写了也不一定发得出来啊。不过这种无奈并不是今天才有的事,翻翻历史就会发现,参茶与创作之间的博弈早已存在。而在某些特殊的年代,这种博弈甚至催生了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——笑话。说到这儿,不得不说说大家耳熟能详的苏联笑话了,那是强拳下民众智慧的结晶,既是无声的抗议,也是无奈的自嘲。苏联笑话有两个巅峰期,分别出现在20世纪初和20世纪七八十年代。比如20世纪初流传的一个经典笑话:一个小男孩问父亲什么是政治。父亲解释说:“就拿我们家来说吧,我负责赚钱养家,所以我是资本家;你妈妈掌管家里的钱,所以她是衙门;我完全掌控你们,所以你们是人民;保姆负责干活,所以她是工人阶级,而你穿着尿布的弟弟,就是未来。”小男孩似懂非懂。半夜,他被弟弟的哭声吵醒,想去找父母帮忙,但父母房门紧闭,他怎么敲也敲不开。他走到保姆的房间,却看到父亲和保姆正在床上光着身体相互撞击。无奈之下,他只能回到自己的床上继续睡觉。第二天早上,父亲问他是否明白了政治的含义。男孩回答:“明白了!资本家正在压迫工人,衙门在呼呼大睡,人民被忽视,而未来一塌糊涂。”这个笑话出自苏布之手,讽刺的是二月革命之后成立的俄罗斯共和国。然而到了1918年,苏布对待笑话的态度来了个彻底转变,苏俄专门针对笑话的“笑话犯”由此诞生。很多人以为苏联笑话的灵感来自西方,其实不然。俄国的幽默讽刺文学有着悠久的历史,18世纪时就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体系,而这种幽默的流传甚至直接推动了盐轮参茶制度的出现。1790年,俄国启蒙运动的重要作家拉吉舍夫出版了《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》,通过对农奴生活的记录,尖锐地抨击了沙皇制度。这本书激怒了叶卡捷琳娜女皇,她下令处死拉吉舍夫,并制定了严苛的参茶制度。俄国文学的底色本是现实主义,其基调深沉而悲怆,颇有唐代诗人杜甫的风格。但在参茶制度推出后,俄国文学不得不转向另一条道路,那便是幽默与讽刺。19世纪,俄国幽默讽刺文学在果戈里的笔下达到了巅峰。他的《钦差大臣》成为经典之作,据说《李卫当官》的灵感便来源于此。书中讲述了一个纨绔子弟在外省被误认为钦差大臣,引发了一系列荒诞的笑料。果戈里曾感慨:“我原本想忠实地描绘现实,但现实一次次让我惊讶。于是,我不可避免地滑向了讽刺。”进入苏联时期,这种讽刺性的幽默被称为“厨房政治”。人们常常在厨房这种私密的环境中,与亲密的朋友吐槽特权阶级的不堪,借此释放积压已久的情绪。苏联式笑话以短小、辛辣、直接见长,尤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众对政治的认知、情感和评价。这些笑话或讽刺物资匮乏,或嘲弄官僚主义,或揭露其腐败无能。比如,有人问:“怎样才能赶走克里姆林宫里的老鼠?”答:“只要挂一块牌子,上面写着‘集体农场’,过不了多久,大多数老鼠会饿死,剩下的也会逃之夭夭。”比如,问:“同志,你对这个问题有意见吗?”答:“我当然有意见,但我不同意我自己的意见。”再比如,有人问伊万诺维奇:“你经常读《真理报》吗?”答:“当然读。不然我怎么知道自己生活得多么幸福呢?”还比如,斯氏、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乘坐火车出门。开着开着,火车突然停了。斯氏把头伸出车窗外,怒吼道:“枪毙火车司机!”可是车还是没有动;接着赫鲁晓夫说:“给火车司机恢复名誉!”车仍然没有动;勃列日涅夫说:“同志们,不如拉上窗帘,坐在座位上自己摇动身体,做出列车还在前进的样子。”又比如,亚历山大、凯撤、拿破仑做为贵宾,参加红场阅兵。——我要是有苏联的坦克,我将是战无不胜的!亚历山大说;——我要是有苏联的飞机,我将征服全世界!凯撤说;——我要是有《真理报》,世界现在也不会知道滑铁卢!拿破仑说。最后比如,戈尔巴乔夫时期。一男子来到酒馆……男子:“来瓶儿伏特加!”侍者:“10卢布。”男子:“上次来还是5卢布,怎么……?”侍者:“伏特加5卢布,另外5卢布是裆的哥命基金。”男人不情愿地掏出10卢布递给侍者。奇怪,侍者又找了他5卢布。男子:“怎么又找了5卢布?”侍者:“酒都卖光了。”不得不说,笑话往往具有鲜明的警示作用。人民的喜恶倾向,在笑话中总能找到直观的体现。如果苏联当局能够从这些笑话中汲取教训并及时改革,或许不至于在短短几十年后轰然倒塌。遗憾的是,他们对待笑话的态度,与沙皇时期并无二致。列氏曾经表示:“笑话对我们的工农国家是有害的。”苏布监察委员什基里亚托夫也在报告中强调:“不要低估笑话对我们的威胁。过去,我们用笑话削弱了旧证券的威信,而现在它被用来针对我们。”因此,苏联建国初期便制定了反哥命罪,并于1926年写入刑法典,第58条的第一款至第十款明确规定,任何传播、制作或收藏此类作品的人,均将接受判刑或流放。这种罪名被民间称为“笑话犯”。据苏安委1990年3月13日公布的数据,1931年至1940年间,共有560675人因该罪名被判刑。而到1953年,因该罪被定罪的人数累计达到370万人,其中79万人被处决。因此,俄罗斯学者将这一时期称为“黑色的年代”,充满“黑色的法庭、黑色的法律、黑色的良心和黑色的天理”。斯氏去世后,赫鲁晓夫释放了部分“笑话犯”。然而到了勃列日涅夫时代,苏联社会氛围再次走向严肃,反而让笑话的数量急剧增长,其中以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笑话居多,占总数的25%左右。1966年KGB成立了第五局,专门负责监控老百姓的盐轮。对于那些散布“诋毁”苏联光明伟大正确的笑话,轻则劳改一年,重则人间蒸发。直到戈尔巴乔夫上台,社会氛围逐渐宽松,笑话才逐渐失去了原有的市场。苏联笑话的流行恰恰说明,高压和强制或许能禁锢人的身体,却无法束缚人的思想。反而越是压迫性的环境,越会激发笑话的产生和传播。在这种环境下,苏联民众的智慧被迫得到锻炼,他们学会了用隐喻、暗示、留白等方式,在字里行间表达自己的思想。因此,苏联笑话成了弱势群体为数不多的精神武器。可以说,苏联笑话就是在“高压锅”里蒸出来的,它是民众在强制环境下的无奈反击,也是生活中苦中作乐的智慧结晶。它不光是让人捧腹的段子,更是一种对现实的深刻认知和讽刺艺术。毕竟,连苏联的高层们自己都承认笑话的威力。只可惜他们只会忙着抓“笑话犯”,却没空发现自己才是最大的笑话制造者。正如果戈里《钦差大臣》里那句台词:“你们笑的,其实是你们自己。”不过,话说回来,笑着笑着,苏联可就没了。作者:一颗躺平的韭菜
人类文明的瑰宝:苏联笑话 最近有粉丝私信抱怨说:“关注你太亏了,你都不能做到日更。”还有粉丝上周日留言:“终于又写长文了。”言外之意我之前那种动辄数千字的长文写的不多了。没错,这点我承认,但我也有无奈和苦衷。就拿昨天来说,我辛辛苦苦码了6000多字,结果一发——直接被拦,怎么改都不行;周一那篇写三百多年前“自挂煤山东南枝”人物的文章,洋洋洒洒5000多字,也发不出去。搞得我写东西都像在拆盲盒,写完了还得祈祷能过参茶,这种把自己辛苦的结晶交给别人决定命运的玩法,一度让我想放弃,后来还是在那位指导我这张又红又专首图的前辈点拨下,让我把打赏开了,用他原话说:“我就没见过谁和钱过不去的。“所以,朋友们,别怪我不写(其实周末我一般会喝大酒,确实懒得写),实在是我有时候就算写了也不一定发得出来啊。不过这种无奈并不是今天才有的事,翻翻历史就会发现,参茶与创作之间的博弈早已存在。而在某些特殊的年代,这种博弈甚至催生了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——笑话。说到这儿,不得不说说大家耳熟能详的苏联笑话了,那是强拳下民众智慧的结晶,既是无声的抗议,也是无奈的自嘲。苏联笑话有两个巅峰期,分别出现在20世纪初和20世纪七八十年代。比如20世纪初流传的一个经典笑话:一个小男孩问父亲什么是政治。父亲解释说:“就拿我们家来说吧,我负责赚钱养家,所以我是资本家;你妈妈掌管家里的钱,所以她是衙门;我完全掌控你们,所以你们是人民;保姆负责干活,所以她是工人阶级,而你穿着尿布的弟弟,就是未来。”小男孩似懂非懂。半夜,他被弟弟的哭声吵醒,想去找父母帮忙,但父母房门紧闭,他怎么敲也敲不开。他走到保姆的房间,却看到父亲和保姆正在床上光着身体相互撞击。无奈之下,他只能回到自己的床上继续睡觉。第二天早上,父亲问他是否明白了政治的含义。男孩回答:“明白了!资本家正在压迫工人,衙门在呼呼大睡,人民被忽视,而未来一塌糊涂。”这个笑话出自苏布之手,讽刺的是二月革命之后成立的俄罗斯共和国。然而到了1918年,苏布对待笑话的态度来了个彻底转变,苏俄专门针对笑话的“笑话犯”由此诞生。很多人以为苏联笑话的灵感来自西方,其实不然。俄国的幽默讽刺文学有着悠久的历史,18世纪时就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体系,而这种幽默的流传甚至直接推动了盐轮参茶制度的出现。1790年,俄国启蒙运动的重要作家拉吉舍夫出版了《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》,通过对农奴生活的记录,尖锐地抨击了沙皇制度。这本书激怒了叶卡捷琳娜女皇,她下令处死拉吉舍夫,并制定了严苛的参茶制度。俄国文学的底色本是现实主义,其基调深沉而悲怆,颇有唐代诗人杜甫的风格。但在参茶制度推出后,俄国文学不得不转向另一条道路,那便是幽默与讽刺。19世纪,俄国幽默讽刺文学在果戈里的笔下达到了巅峰。他的《钦差大臣》成为经典之作,据说《李卫当官》的灵感便来源于此。书中讲述了一个纨绔子弟在外省被误认为钦差大臣,引发了一系列荒诞的笑料。果戈里曾感慨:“我原本想忠实地描绘现实,但现实一次次让我惊讶。于是,我不可避免地滑向了讽刺。”进入苏联时期,这种讽刺性的幽默被称为“厨房政治”。人们常常在厨房这种私密的环境中,与亲密的朋友吐槽特权阶级的不堪,借此释放积压已久的情绪。苏联式笑话以短小、辛辣、直接见长,尤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众对政治的认知、情感和评价。这些笑话或讽刺物资匮乏,或嘲弄官僚主义,或揭露其腐败无能。比如,有人问:“怎样才能赶走克里姆林宫里的老鼠?”答:“只要挂一块牌子,上面写着‘集体农场’,过不了多久,大多数老鼠会饿死,剩下的也会逃之夭夭。”比如,问:“同志,你对这个问题有意见吗?”答:“我当然有意见,但我不同意我自己的意见。”再比如,有人问伊万诺维奇:“你经常读《真理报》吗?”答:“当然读。不然我怎么知道自己生活得多么幸福呢?”还比如,斯氏、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乘坐火车出门。开着开着,火车突然停了。斯氏把头伸出车窗外,怒吼道:“枪毙火车司机!”可是车还是没有动;接着赫鲁晓夫说:“给火车司机恢复名誉!”车仍然没有动;勃列日涅夫说:“同志们,不如拉上窗帘,坐在座位上自己摇动身体,做出列车还在前进的样子。”又比如,亚历山大、凯撤、拿破仑做为贵宾,参加红场阅兵。——我要是有苏联的坦克,我将是战无不胜的!亚历山大说;——我要是有苏联的飞机,我将征服全世界!凯撤说;——我要是有《真理报》,世界现在也不会知道滑铁卢!拿破仑说。最后比如,戈尔巴乔夫时期。一男子来到酒馆……男子:“来瓶儿伏特加!”侍者:“10卢布。”男子:“上次来还是5卢布,怎么……?”侍者:“伏特加5卢布,另外5卢布是裆的哥命基金。”男人不情愿地掏出10卢布递给侍者。奇怪,侍者又找了他5卢布。男子:“怎么又找了5卢布?”侍者:“酒都卖光了。”不得不说,笑话往往具有鲜明的警示作用。人民的喜恶倾向,在笑话中总能找到直观的体现。如果苏联当局能够从这些笑话中汲取教训并及时改革,或许不至于在短短几十年后轰然倒塌。遗憾的是,他们对待笑话的态度,与沙皇时期并无二致。列氏曾经表示:“笑话对我们的工农国家是有害的。”苏布监察委员什基里亚托夫也在报告中强调:“不要低估笑话对我们的威胁。过去,我们用笑话削弱了旧证券的威信,而现在它被用来针对我们。”因此,苏联建国初期便制定了反哥命罪,并于1926年写入刑法典,第58条的第一款至第十款明确规定,任何传播、制作或收藏此类作品的人,均将接受判刑或流放。这种罪名被民间称为“笑话犯”。据苏安委1990年3月13日公布的数据,1931年至1940年间,共有560675人因该罪名被判刑。而到1953年,因该罪被定罪的人数累计达到370万人,其中79万人被处决。因此,俄罗斯学者将这一时期称为“黑色的年代”,充满“黑色的法庭、黑色的法律、黑色的良心和黑色的天理”。斯氏去世后,赫鲁晓夫释放了部分“笑话犯”。然而到了勃列日涅夫时代,苏联社会氛围再次走向严肃,反而让笑话的数量急剧增长,其中以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笑话居多,占总数的25%左右。1966年KGB成立了第五局,专门负责监控老百姓的盐轮。对于那些散布“诋毁”苏联光明伟大正确的笑话,轻则劳改一年,重则人间蒸发。直到戈尔巴乔夫上台,社会氛围逐渐宽松,笑话才逐渐失去了原有的市场。苏联笑话的流行恰恰说明,高压和强制或许能禁锢人的身体,却无法束缚人的思想。反而越是压迫性的环境,越会激发笑话的产生和传播。在这种环境下,苏联民众的智慧被迫得到锻炼,他们学会了用隐喻、暗示、留白等方式,在字里行间表达自己的思想。因此,苏联笑话成了弱势群体为数不多的精神武器。可以说,苏联笑话就是在“高压锅”里蒸出来的,它是民众在强制环境下的无奈反击,也是生活中苦中作乐的智慧结晶。它不光是让人捧腹的段子,更是一种对现实的深刻认知和讽刺艺术。毕竟,连苏联的高层们自己都承认笑话的威力。只可惜他们只会忙着抓“笑话犯”,却没空发现自己才是最大的笑话制造者。正如果戈里《钦差大臣》里那句台词:“你们笑的,其实是你们自己。”不过,话说回来,笑着笑着,苏联可就没了。作者:一颗躺平的韭菜